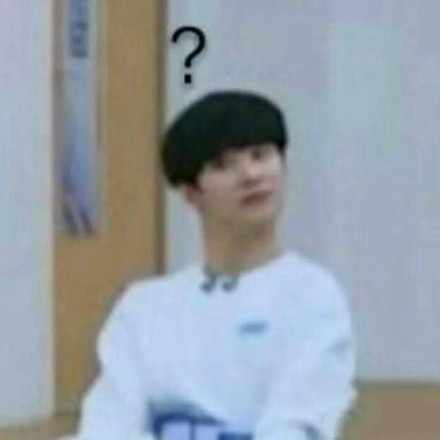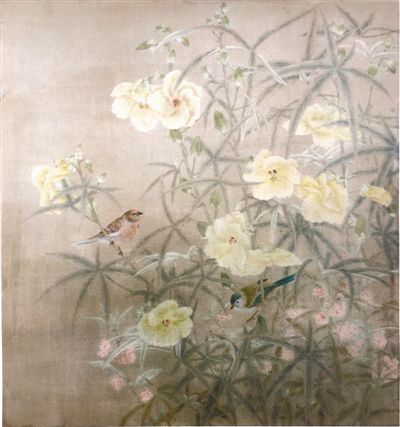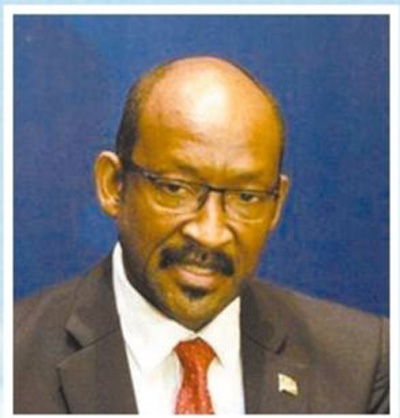就在錢報記者探訪養殖基地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10日,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三文魚分會宣布正式成立,與之共同露面的,還有國內第一個《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表示,該標準得到了農業農村部漁業漁政管理局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指導與支持。
隨著網絡爭議再度升起,除了“虹鱒魚到底屬不屬于三文魚”這個核心爭議之外,公眾更關注的是知情權和選擇權,以及這個團體標準是否具有約束力;業界關注的則是國產三文魚和進口三文魚的市場份額之爭——在業內人士看來,由于三文魚市場的潛力,風波再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國內三文魚產業的快速發展,開始搶占原本以進口為主的市場份額,影響到了進口商的利益。
行業制定團體標準
定義“三文魚”范圍
8月10日,青海共和縣,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三文魚分會成立大會會場外,崔和介紹,國內首個《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公布,如無問題,今年9月10日后正式實施。
這在現場很多人看來,是對那波輿論風潮的行業整體回應。并且,雖然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會長崔和依舊反對就此事對外進行辯駁,但同時坦言正是因為此次風波,推動了行業標準的加速出臺。
除了正式發布團體標準,青海民澤龍羊峽生態水殖有限公司作為國內最大的三文魚(虹鱒)養殖企業,成為這個分會的首任會長單位。該公司董事長、首任會長應米燕在大會發言時指出,持續的爭議也反映出中國三文魚產業缺少統一標準,還有待進一步規范。
那在這份團體標準中,到底如何定義了“三文魚”?
記者看到,《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中明確寫明,基于科學分類和命名方式,三文魚是鮭科魚類的統稱,包括大西洋鮭、虹鱒、銀鮭、王鮭、紅鮭、秋鮭、粉鮭等。
同時,《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的制定也因市場需求對寄生蟲進行了嚴格規定,針對目前我國水產品中對人類健康危害較大的寄生蟲——線蟲、吸蟲和絳蟲,結合寄生蟲的生活史,參照GB10136中即食水產品中寄生蟲的要求,對三種寄生蟲的感染人體階段(吸蟲囊蚴、線蟲幼蟲及絳蟲裂頭蚴)進行了限定,要求不得檢出,從而保護消費者食用安全。
崔和說,這個團體標準還對產品感官指標、理化指標、安全衛生指標等做了嚴格要求。對產品標簽也作出明確要求,必須標注原料魚產地以及種名,讓消費者清楚原料魚來自哪里,知曉產品的商品名及種名,“產品包裝上會寫三文魚,‘三文魚’這個表述后面會有括號,里面標注上魚類品種。”崔和指出,只有超過三公斤的虹鱒魚才能被稱為三文魚,以及在保證食品安全情況下生吃。
“標準的發布,與此前那場風波,有著必然聯系。”一位參會的鮭魚養殖企業負責人說,如果沒有這樣的行業標準,他們很難說服輿論相信國產的“三文魚”是能保證品質的,生食亦無問題。同時他不否認,這是為了保護國產三文魚養殖企業能在行業自律前提下有更好的發展,“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前所未有的高,所以消費者必須有知情權和選擇權。”
質疑接踵而來
這標準靠譜嗎
但正是這份《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再度引發爭議。
首先,起草并發布這份團體標準的,是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和13家相關企業,這對不少民眾而言就存在質疑;其次,上海海洋大學教授陳舜勝認為,上述團體標準中,消滅寄生蟲方法屬海水魚方法,對于淡水魚依據不充分;第三,這是一份團體標準,按照2018年1月開始實施的新版《標準化法》,團體標準是由社會團體協調相關市場主體共同制定的,由本團體成員約定采用,或者供社會自愿采用。所以這既不是必須強制執行的國家標準,也不是受認可程度較高的生物學分類學術標準;最后一點,也是核心老問題:虹鱒魚是否能“游入”三文魚序列?
對此,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會長崔和表示,淡水養殖三文魚寄生蟲多過海水魚,純屬謠言,沒有實際檢測數據的依據。今年廣東省權威檢測部門專門對包含海水及淡水養殖的260多個三文魚樣品進行檢測,均沒有發現寄生蟲問題,“另外,從微生物的角度來看,國產三文魚有地理區位上的優勢,運輸時間可控,安全性也會更高。”
此外,記者從協會方面了解到,這次會議以及標準的制定過程中,起草單位包括養殖、加工、進口及飼料企業,代表了全產業鏈,養殖經營品種包括虹鱒、大西洋鮭等(標準中所有品種),在起草后的審核階段,則是由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專家們把關,并且標準是在農業農村部漁業漁政管理局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指導與支持下制定的,同時得到學界專家的審議和認可。
而根據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解釋,標準包括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團體標準、企業標準。國家標準分為強制性標準、推薦性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是推薦性標準。
此外協會也表示,目前團體標準的制定,是走向標準化、規范化的一大步,以后逐步上升為行標、國標,這是努力的方向。
前珠江水產研究所副所長白俊杰則認為,有標準總比沒標準好,但還要完善以及后面怎么執行這個標準、檢查、監督,這是需要跟上的。
背后或是市場之爭
中國三文魚消費市場前景廣闊
回應之外,不少國產三文魚企業都提及風波源自市場競爭問題。對此,崔和與應米燕等協會成員也婉轉表達了這個觀點。而從事三文魚養殖的康樂綠鄉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張建新則在此次會議上直指,一些進口商不要再以“真假”的名義借助網絡故意進行炒作,“虹鱒比大西洋鮭賣得貴,所有的魚養殖不好都會存在寄生蟲,尤其是野生三文魚。”
實際上,三文魚在中國市場上的走紅,并算不上久遠。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趙依民至今記得,三文魚在1994年時國內根本沒市場, “我們在廣州做三文魚推廣時,當時一位水產局長問我,你這三文魚跟三明治有什么關系?我只能說也可以做三明治。”
然而目前,中國三文魚年消費市場增速達25%,預計2025年中國三文魚的消費總量可能超過25萬噸,市場前景十分廣闊。未來幾年,中國市場將成為三文魚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而滿足國內市場對三文魚產品的需求,仍主要依靠進口。
5月風波乍起時,一位不愿具名的國產三文魚企業主告訴錢報記者,與其說那是單純的一場科普論戰,還不如說是一場商業之爭,“進口三文魚與國產三文魚的市場之爭,即便國產三文魚市場逐步發展起來,也不足以威脅進口三文魚市場,但關鍵是終歸誰都不愿意自己的蛋糕被瓜分。”
但崔和估計中國目前每年的三文魚銷量在10萬噸到12萬噸,國產和進口比例約1:10。專門做生食的三文魚,國產量在1萬多噸左右,進口量則在4萬噸左右,“未來國產三文魚的量可能會提高,但份額比例應該不會變。”
趙依民也坦言目前市場上的確出現了一些競爭,但并不激烈。
挪威海產局專家博薇婭告訴記者,她認為目前中國國產三文魚的養殖還不會對挪威出口中國三文魚的市場產生影響,不過這對整個三文魚行業而言是一件好事,能把市場蛋糕做得更大。
采訪中,多位國產三文魚企業負責人認為,目前的網絡輿情,“與三文魚進口商和國產商都無利。”
發酵至今,這場論戰并未因此消停。不過學界、業界和輿論在一個問題上倒是越走越近——公眾更關注的還是對產品的知情權、選擇權,以及食品安全。